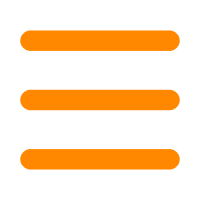自从C.P. 斯诺、萨顿诸人倡言科学与人文已形成两种文化以来,几十年倏尔过去,论者自论之,科学与人文的歧异,却好像有增无已。1986年的《威尼斯宣言》称:“研究自然体系而形成的世界观,与人文学术和社会日常的价值观之间,呈现重大歧异,对人类存活已构成威胁。”
此种分歧与危机,不只表目前外部,即科学一同体与人文一同体之间很难交流,而且更深刻地表目前内部,即科学作为求知体系,其客观基础与主观的人文历史原因之间的张力已经表面化,而使科学的理性基础遭到质疑。尽管近年来人类的技术力量呈空前的膨胀式进步,然而科学的自信,科学在学术中的尊严,却已空前低落。十八世纪诗人颇普所谓“上帝说要有牛顿,于是有了光。”的那种对科学的崇敬,十九世纪对科学文明进步的信念,与本世纪中期以前对科学靠谱基础的信心,皆已遭到种种批判而发生动摇。
科学的定义更迭
虽然对基础主义的批判发韧于科学哲学家如卡尔·波帕,然而科学内部的理论定义发生重大更迭,则属先行。1905年爱因斯坦已完成狭义相对论。1915年他发表的数学理论已将相对论推广到引力加速运动。量子力学的基本完成时期约在1900至1927年之间。哥德尔定理发表于三十年代初期。诸这样类的理论所提出的新观念,已足以扰乱既有些科学秩序。
本来,就物理科学而言,新理论所更迭的只不过古典的物理学定义,如:绝对时空、以太、引力即时效应、欧几里德空间常见有效、光按直线投向空间、物体无最大限度速度,诸这样类。而且新理论并不可以取代古典力学在一般范围里的应用。譬如海森伯格测不准原理的方程为:
D c ·D r ³ ¾ p
其中 D c 为一电子地方测定误差,D r 为其动量测定误差,h为普朗克常数。电子地方测定越准确,则动量测定越不准确。因为直线动量为水平乘速度,故不可能同时测定电子的地方与速度。同理,亦不可能同时测定电子的能量与具备此能量的时间。然而因为普朗克常数的值极低,约为6.625×10 尔格/秒,故这个原理仅适用于原子以下的微观范围,对牛顿力学范围的计算并无实质意义。但在哲学观念上,其意义则远不仅此。传统上觉得,逻辑的常见性在于,逻辑的基本原理、公理、定理适用于所有可能世界。假如在一个范围里某基本原理已不适用,则逻辑的常见性便已成为问题。海森伯格方程、薛定鄂方程、玻尔理论对同一律、排中律提出挑战。因而对整体与局部的关系这个定义,与非此即彼的传统分类法,甚至对物质及其客观性,也提出质疑。而这所有又与相对论扬弃绝对时空有关。传统分类法以排中律为基础,事物非此即彼。但粒子的地方与速度不可以如此简单分类。传统所谓整体包涵局部,指一实体在空间或时间上包涵之。相对论和海森伯格方程则觉得,一实体处于另一实体的时空域之内,为包涵关系。玻尔觉得,电子既是粒子又是波,在逻辑上矛盾,但在经验中是事实。海森伯格的测不准原理可以理解为,粒子仅有统计性的地方;但也可以理解为,仅当有人察看它的时候才有地方。相对论的水平依据在运动中的速度相对于察看者,也说明物质的形态依靠于察看者。对原子结构的认识,无论汤姆逊、卢瑟福、玻尔模型,皆是理论建构,而非原子本身。粒子是合适薛定鄂方程之物。物质的外延不清,客观性模糊。
更有兴味的是,纯数学理论也得出类似结果。非欧几里德几何的出现,使几个几何体系适用于同一人类空间经验。汉密尔敦的四元数理论证明a×b ¹ b×a。略文海姆-斯寇姆理论证明,一个公理的集合可以导出本质上不一样的讲解理论。哥德尔定理觉得:一,在任何一个数论的形式体系中,皆有一个真公式,即不可确定性公式,其本身不可证明,其否定式亦不可证明;二,在数论的形式体系中,其一致性不可能在该体系中证明。假如推而广之,彷佛可以说,一个理论体系,求其一致则不完整,求其完整则不同;一个理论体系的一致性只能在体系以外得到证明。也就是对矛盾律的常见性提出质疑。亚里士多德的科学理想,便是在同一律、矛盾律、排中律和词项概念不变的基础上,依据自明的理性首要条件推导出常识体系。直到现代逻辑经验论亦觉得,理性与直觉经验是常识的靠谱保证,而理性便是逻辑性。假如逻辑性遭到质疑,则作为求知靠谱基础的理性便已发生动摇。
批判与深思
科学内部既已发生重大变革,对于此种变革的哲学深思,加上其他社会条件,也就顺势形成一股对于科学的靠谱基础,乃至对理性,甚至对西方文化的所谓现代性,进行批判的思潮。远在四十年代,卡尔·波帕已提出证伪理论,以批判当时公认的办法论。他否定总结法,觉得总结根本没有。常识的获得只不过通过错误假说的被否定。“从变形虫到爱因斯坦,常识的增长从来相同。”“动物的常识,前科学的常识,其增长以消灭持有错误假说者为代价;而科学的批判,则常以理论代人受难,在错误信念将吾人引向毁灭之前先行消灭它们。”(Karl Popper, Objective Knowledge, Oxford, 1972, p.261)既然总结性的因果被否定,科学也就难有确定的基础。波帕把科学家比作给自己房间画地图的人。他需要把他正在画的地图也包含在这张地图之内。“他的任务不可能完成,由于他需要把他画地图的最后一笔也画在地图里面。” 这是对逻辑经验论那种充满自信的证明理论的讽刺性写照。然而总结法作为一种办法方案,不止是科学求知中历来行之有效的方法,而且也蕴涵于证伪办法之中。“所有天鹅皆为白色”这个判断,只须发现一只黑天鹅便可以证伪。然而若要确立这个全名判断,与在黑色鸟类中确认一只黑天鹅,皆不能离开总结办法。后来,波帕的学生氨纶托斯试图用“研究纲领”来讲明科学常识的内容增长,然而亦未能提出统一的常识标准。
六十年代初期,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科学的进步据称是因为“科学范式”的更迭。科学一同体从同一模式中学习专业常识,依据同一模式从事科学研究,同意相同的实践规则的制约。建构理论和设计证明,不再是依据逻辑经验论所谓的统一办法,而是科学一同体在肯定历史社会条件下一同遵循的“范式”。科学范式中有若干社会心理原因,不在理性办法控制之内,故科学常识的增长没确切的理性基础。不同年代的范式之间不可通约,彷佛科学进步没连续性。然而历史事实并不是这样。譬如牛顿体系的“水平”不变,相对论的“水平”依据运动的速度而变化,二者并不同义。然而两个术语指称的却是同一物理现象,只不过相对论的“水平”从是一个更为确切的讲解理论,其说明域超越牛顿力学的低速范围。又如,吉尔伯特、弗兰克林、麦克斯韦理论中的“电”定义十分不同,但三个术语的外延指向同一物理现象。于此可知,不同年代的理论之间并不是没一同的理性基础。
蒯因的“翻译不确定论”既欲说明不同文化语言之间的翻译不可能,又欲说明不同理论之间的不可通译。蒯因最后诉诸外在的行为主义标准,彷佛在语言逻辑的使用方法中没一同的理性基础。然而对外在行为的察看、判断、陈述、验证皆需要通过本己的语言。可见不同语言之间仍有一同的理性基础。蒯因则觉得理论之间没相通的理性基础,常识的来源只不过感觉。“没有外在的基点和第一哲学。”(W.V.Quine, ontological Relativity, New York, 1969, p.127.)“自然科学说世界是什么,就是什么。只须自然科学是正确的,而大家判断其是不是正确大体取决于预测的经验检验,便是这样。” “不论自然科学的可错性怎么样,自然科学的一个发现是:吾人关于世界的常识只不过感觉同意器所受的影响。” 在早期的《经验论的两大教条》中,蒯因觉得,吾人所谓的常识,乃是一个人为架构物。科学理论的中心是形上学陈述和数学逻辑陈述,其外一层为物理学陈述,更外层为经验陈述,最外层与经验相接。其中任何陈述皆不与具体经验一一对应。原则上可对任何部分的陈述作出足够的调整以适应相反的经验。彷佛常识的结构与实在的结构之间没确切的关系。然而事实上,新的理论成功地代替旧理论,正是新理论的结构更确切地说明实在结构的原故。牛顿三定律可以导出150多个命题,讲解很多地球和天体现象。但凡可用相对论代替这类讲解的地方,皆是新理论更确切讲解实在的地方。
费耶阿本则反对所有办法。他觉得不可能有预设的合理性标准。科学真理只不过一种修词,并无客观内容。但他又承认科学的成功。不过,这种成功只不过因为科学父母期不懈地研究某一问题的结果。他们的过分之举,总会被其他学派的过分之举所抵消。费耶阿本称,他可以否定科学真理,而把这个判断当作真理提出来,犹如他可以用德语来宣称德语不如拉丁语。他忘了,真值不是一种语言,而是使各种语言得以通译的理性标准。正由于客观上存在这种标准,他才可以把“反他们法”当作一组真陈述提出来。他却倡导科学无需任何理性标准,All goes!所以库恩称之为vaguely obscene。
晚近的办法论研究,多探索怎么样重建理性标准。厦皮尔、劳丹等人便是这样。劳丹批评库恩、费耶阿本对历史连续性的忽视。他提出“研究传统”,其中既包涵科学理论,又涵容本体论体系。然而他忽视统一的逻辑和对应规则,故在科学术语的陈述与本体论陈述构成真问题有哪些用途中,未能提供统一标准。譬如数学证明和历史讲解之间怎么样对比,便成为问题。近年语义派的科学哲学家如萨普斯、斯尼德、范弗拉森、史泰格缪勒等以集合论方法进行公理化,似尚未获得公认结果。
总之,由坎贝尔、赖欣巴赫、卡纳普等人代表的逻辑经验论“标准办法论”,在六十年代已遭到彻底的批判。批判的重点大概在:科学术语区别为察看语言和理论语言,在语义学上没依据;理论术语不需要语义规则概念,并无依据;对应规则的特殊语义功能没依据;察看语言由对应规则概念,不可能不遭到理论的渗透;科学理论被当作完成的科学报告,而非历史中科学一同体的建构物,与史实不合;公理化的必要性遭到质疑。这类批评多半可以讲解为,被“标准办法”排斥于科学理论以外的人文价值,事实上在科学理论之内。
科学原是人文理想
人文价值不只在科学的理论构成之内,而且可以说,科学本身原是一种人文理想。科学不是自然的产物。在自然演化中,不可能自发产生科学。科学是文化,而且是特定文化的产物。所谓人文,humanitas,原指人类;引申为人性,人的情感;转为人的文化、教养、教育。汉语“人文”,指礼乐教化,如《易·贲》:“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孔颖达疏:“言圣人察看人文,则诗书礼乐之谓,当法此教而化成也。”乃是更狭义,专指儒家教化。广义的人文则指人类文化的内涵,与有关的学术艺文。
人类科学产生在古时候希腊,有一些明显的必要条件。人要系统地揭开自然之谜,必对自然有一种对象化的好奇之感。假如只把自然视为与人一体,则必流于感悟冥思,不会视为研究对象(在结构上可以分解明确的“物”)。这便需要一种主客二分的语境。古希腊恰有这种发达的语境。第二,必有一种信念,确信人是理性动物,而自然有着内在的理性结构,故人可以系统地揭示自然。古希腊恰有这种哲学。除此之外,古希腊人恰有一种以数学方法揭示最深刻的真理和世界结构的信仰,而又恰有欧几里德几何这一发达的公理化体系。亚里士多德科学,便是从理性首要条件出发,以公理系统演绎方法,全方位揭示有着内在理性秩序的自然的一种价值理想。如此的科学,必源于如此的文化语境,和如此的人文理想。科学的发生,源于对自然的好奇与理性求知的态度,与借助自然和生产力无关。科学与借助自然的态度结合起来,此事发生相当晚,乃是出于另一种价值理想,即基督教信仰。
基督信仰对科学进步的影响,约有三个方面。一,世界是上帝的受造物,故世界本身是一种contingent(偶性的,可存在可没有的)存在。二,世界虽为偶性存在,却不是任意紊乱的存在。理性的上帝创造了具备内在理性的世界,并按上帝形象创造了人类,故理性的人类可以全方位揭开世界之谜。三,人类是上帝救赎计划的中心,自然是人类借助的对象,“你们要生养很多儿女,使你们的后代遍满全世界,控制大地。”(现代中文译本《旧约·创世纪》1)
此种观念,显然与希腊思想不同。希腊人对于自然的兴趣在于求知,而基督教文化对自然的态度则是借助控制。希腊人觉得自然为势必存在,故可以通过公理系统演绎方法推导出关于自然的常识;而基督教文化则觉得世界是偶性存在,故需要通过经验的方法一点一滴地揭开自然之谜。惟其希腊的科学理想是演绎推导,故希腊人不感兴趣作实验。欧洲最早的实验科学,产生于中世纪的修道院。亚里士多德关于落体的速度取决于重量的错误理论,上下一千年,竟无人费神去验证一下。直到伽利略的年代(也就是基督教文化的科学理想上升的年代),才被实验证伪。
然而古希腊的科学理想,却并未由于实验科学的产生和进步而整体上消逝。自此而往,科学作为一种人文理想,一直处于西方文化两大渊源的交互影响之下。亚里士多德关于求知的确切理性基础,关于“欧几里德支点”的信念,公理化体系中蕴涵的简单性原则(以最少首要条件建构理论),与柏拉图和多数希腊哲学家关于几何形式和谐完美的理想,这类理念的生命很悠久,可以说直抵今日。不只希腊和希腊化年代,而且中世纪和文静复兴年代的科学理论,也大概(并不是仅仅)是此种科学理想的产物。只不过不同理论在构成时,对这种理念的理解和解释不同。哥白尼正是深感托罗密体系在数学上不和谐,才着手对之改造,而他也正是受着圆形这个完美几何形式的限制而未能打造椭圆形天体轨道模型。开普勒的行星运动定律揭示出宇宙在数方面的和谐比率:行星矢径在相等相间扫过相等面积、行星公转周期的平方正比于与太阳距离的立方、行星远日点和日前点之间角速度的变化用乐谱形式标出。牛顿正是继承此种思路,从行星运动定律中导出具备数的和谐的万有引力定律。现代科学理论,如电磁场结构理论,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引力场方程乃至未成功的统一场论,巴尔末公式,量子力学矩阵方程,分子生物学大分子立体结构理论等,皆与上述人文理想或本体论理念有关。科学家总是觉得,数学上美的形式在描述世界方面有价值。迪拉克正是在对称和谐的美学理想推进下,预设反粒子的势必存在。
不只科学本身原是一种人文理想,而且科学理论的建构,亦必以基本的形上学前设(如自然规律性、齐一性等)为必要条件。除此之外,科学理论的建构,总是以美学理想或本体论理念为出发点或启发动力。再者,科学一同体所遵守的规范体现某些伦理价值,与诸这样类,也是科学中的人文理想,此处不遑多论。人文价值对于科学理论的关系,有二特征:既发展又限制理论的视线,既可有益又可有害;常以潜首要条件或背景常识的形式影响理论,鲜有作为公理或辅助假说而纳入公理体系者。
价值与事实
将科学中的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分开,并且力图将价值原则排除出科学以外而不承认之,此事发生颇晚。早期的自然哲学或科学,并不排除价值。柏拉图的常识论,以理念为基础,而最高理念则是善的理念。求知与求善相统一。亚里士多德以科学为探求世界势必真理的公理体系,而求知本身便是最高幸福。中世纪的科学家为修道士。文静复兴年代的科学家,既援引希腊的人文理念,又是真诚的教徒。十六七世纪的科学家如笛卡尔,其体系多援引教义。大概十八世纪是将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分开的决定性年代。然而始作俑者,似是十三世纪的阿奎那。在《神学大全》中,他详细论证自然常识靠理性之光,不靠启示,也就赋予科学求知以独立于价值的性质。十三四世纪的经验论者和唯名论者也多有类似的见解。经验论的传统在英国不绝如缕。十八世纪的休谟乃起而在逻辑上证明价值陈述不可能从事实陈述中推导出来。康德将科学与伦理、文静、宗教分开。十九世纪以来,价值与事实的离别,遭到两方面的推进。非理性论者如尼采,强调这种离别,而实证论者也多看重这种离别。直至逻辑经验论派,则觉得形上学陈述没意义,价值只不过主观情感或态度,科学为价值中立的常识体系。石里克觉得,伦理学也是科学,伦理学家的最大危险便是成为道德家。0訋0g?/p>
六十年代以来,科学中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的离别,已遭到所谓历史主义,乃至所谓后现代思潮的彻底批判,至于达到矫枉过正的程度。不久前,一位著名科学哲学家在普林斯顿演讲,听众中有人提问:你的口气彷佛说科学和理性及实在有关?现在在西方的一般建议,大概觉得科学陈述为工具性,也就是对科学中的事实原则十分怀疑。此与实用主义传统有关。皮尔斯倡导,真理的界定最后是协议的产物。杜威则称,所有常识皆为工具性。除此之外,与后现代思潮有关。R.罗蒂称:“科学根本不是人类理性的典范,而是‘大家协议’的典范。” 费耶阿本宣称,科学真理只不过修词,并无客观内容。与诸这样类。
实质状况是不是这样?科学理论构成中,确实有价值原因,科学有隐含的或自觉的价值原则,已如上述。科学的所谓察看语言,并不是中立。察看术语由理论概念。比如根据所谓标准办法论,气体分子运动理论的一个公设是: ,读为“凡气体皆为分子组成”。其中察看术语G被该理论的语义规则概念为“一个气体标本的属性”,如此,对应规则语句中的察看术语也就不是独立于理论的中立语言了。然而尽管这样,成功的科学理论,一直与平时语言中的实在有着操作性的对应关系。这种操作,在不同社会,不同文化语境中,可以同样达成。一个科学实验,不论其程序设计、仪器制造、察看条件遭到怎么样的理论影响,也不论其结果中包涵怎么样的理论解释,然而同一实验既然可以在不一样的社会条件下重复,也就说明该实验不是一个社会学的过程。理论“渗透”察看,也不势必影响察看的有效。著名的实例是太阳中子接收实验。这里,“弱互用途理论”既是设计接收器的察看理论,又是待验证理论。根据“循环验证”的假设,实验结果应与理论的预测一致。然而实验结果却并不同。一个科学理论总是是一个复杂的公理系统。一个实验不可能验证全系统,而是验证其未知部分。只须察看理论没影响这未知部分,便不会干扰实验的有效。
价值原则与事实原则是科学的两大原则,不可偏废。价值原则体现于本体论或基本首要条件。事实原则虽然也是一种价值理想,却贯彻于理论和察看的全过程。无论讲解理论、察看理论或察看操作,皆必贯彻事实原则,科学方能与平时语言中的实在发生可操作的对应关系。勿论问题的提出、理论的建构、逻辑的推导中涵有怎么样的价值原因,也勿论察看与证据中涵有怎么样的解释成份,在理性批评精神和事实原则的引导下,科学家总大概在肯定时空条件下诉诸最可信的原因和证据,在理论和经验的不断扩展中发现和纠正错误,对进步中让人理解的实在之结构获得愈加深刻的认识。
认识与真理
事实原则使科学诉诸理性、逻辑和经验证据。理性作为秩序原则,其内涵在历史中有所进步,但迄今并未能废弃秩序原则。所有所谓非理性的力图废弃秩序原则的论证或语句,只须能叫人了解,必诉诸秩序原则,而秩序原则的核心便是逻辑性。
逻辑性是蕴涵于语言中的基本约定。逻辑理论在历史中进步,人对逻辑规律的理解不断深化,但只须语言尚在,逻辑性亦不可废弃。笔者曾做过一个非实验室条件下的简单实验。对象是一岁半到两岁、正在掌握说话、智商进步好的儿童。办法:一,以纸板做成一个圆形、一个正方形。二,以圆形出示一个儿童,教他(她)说“这是圆的。”重复几遍,直到问他(她):“这是什么?”他(她)能立即说出:“这是圆的。”三,以同样方法教会他(她)认出正方形。四,出示圆形,问:“这是否又是圆的又是方的?”他(她)回答:“不是又是圆的又是方的,是圆的!”然后出示方形,结果大概相同。上述实验或者能够帮助说明,逻辑性乃是与语言同时掌握的一种基本约定。语言在,逻辑性便在。逻辑规律和理论,是对逻辑性的体系化。正如其他理论,逻辑理论也可错,可进步,可纠正。有人或者觉得,哥德尔定理之类的数学理论已经证明矛盾律无效。其实哥德尔正是严格遵循矛盾律而推导出其定理。否定矛盾律,也就否定其定理的基本首要条件。哥德尔定理仅仅否定在一个数论体系内部证明该体系一致性的可能性。当代对逻辑性已有前所未闻的深刻理解,这对于科学理论的意义,不在于舍弃逻辑性,而在于:不可将逻辑视为在所有可能世界中求得靠谱因果性的先验保证。人所了解的逻辑,是人类语言约定的最基本秩序原则及其体系化,却未必是世界结构本身的秩序原理。现在人类对世界的认识是不是处于初级蒙昧阶段,这个问题,因为缺少整个世界的资料,根本没办法回答。以人类语言约定的秩序原理来规定世界的势必性,是对世界的一种无理强制。此种倨傲是欧洲理性主义的致命弱点,其渊源既源于宗教信仰又源于更古老的本体论。所幸者,现代人类智慧对此已有较为清醒的认识。在科学研究中,大家需要遵循现有些逻辑规则,来进行所有思维和操作,同时又不可以以此来预设所有势必性。在研究的肯定阶段,凡依据充足理由和证据而成功地得出的因果系列,不论与当时逻辑信念是不是一致,亦应同意其势必性。量子理论修订分配律,便是一个实例。正如大家不可能为信念提供证明,却需要同意价值原则一样,大家也需要同意逻辑原则,由于若没这类原则大家连一步也迈不出去。这便是人类理性的两难处境。
那样科学常识有没真理性?假如科学理论有价值前设,察看受理论影响,而逻辑是语言约定,那样怎么样保证科学常识不是循环论证和验证,而是对客观实在的结构之认识?这已经涉及认识论及真理标准问题。自本文目的而言,仅能最扼要地陈明笔者的理论。
人与世界的接触,仅能通过感觉同意器,而感觉同意器所同意的是简单的印象。即便简单的印象,也已经加工组织过。世上没纯粹的感觉。感觉中涵有预期,而人的预期受语言中的观念影响。连什么是“正常”的感觉,也由不一样的理论规定。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康德的先天综合原则,马赫的感觉要点,牛顿的绝对时空,董仲舒的“以类合之,天人一也”,王阳明的“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凡此皆影响人的感觉。同理,科学通过察看与世界的接触,无论感觉的范围倾向,仪器的架构,抑察看的办法,皆受理论的规定。建构理论需要通过秩序原则、价值原则、事实原则等等,与特定历史中的常识构成、科学规范,加以个人的想法创造,其中有若干非理性控制之内的原因。“从经验到基本假说没逻辑通路。”最后验证需要通过证明理论。归根结蒂,科学并未与实在本身发生任何接触。科学的所有活动,皆在人的理性、价值、语言之内。“我的语言的界限,便是我的世界的界限。”然而一种理论可以通过不止一种逻辑来公理化,理论不等于理论的陈述。一个实验可以在不同社会条件下重复。科学的应用常见于任何文化语境。凡此皆说明,科学常识并不绝对囿于语言之内,而与“人的”以外的世界有一种操作性的对应关系。科学常识的这种客观性,不是“协议”、“工具性”、“循环验证”所可以讲解。某些哲学家否定这种常识的真理性,似是受制于理性主义的传统,彷佛不符合“势必”原则的便不可能是真知。
科学常识的获得,便是人类本身的秩序原则,加上种种辅助原则,与理论指导下察看到的世界的秩序之间,反复对比验证的结果。换句话说,便是人与世界之间主客互动的理性求知活动之结果。世界的实在性,天人之间主客互动,理性求知、知行不离、动态综合的真理标准,这类观念皆来自中国的文化理想。真理的规范并不是单一静止的“符合”、“一贯”、“工具”,而是主客互动无穷往返的系统性对比。真理不是静止的“上帝之眼”所获得的势必性,而是主客互动无穷往返过程中的势必联系。没实在客体,便不可能有这种互动,也就没真理。故真理不可能是协议或工具。然而实在并不是物自体的自我呈现,而是主体依据自己的秩序原则和理论设计而察看到的实在,这实在已经包涵主客互动。故真理不可能是符合。真理是无穷过程中的势必性,故不可能是静止的一贯。这无穷互动包涵可错和自我纠错,主体的认识恒常指向实在,益趋真切,故具真理性。这种互动又并不是改造世界。因改造必在认识之后,犹如必先做好衣服才能修改。这种互动便是认识本身。
中国文化的机会
假如希腊的人文理想和基督教信仰过去启发出这样辉煌的科学创造,大家中国的伟大文化为何不可以启发出同样伟大的科学?诸如惠施十事之类的精微思辩,较之古希腊的形上思辩,并无逊色。墨经逻辑之缜密,亦不逮于古希腊逻辑。老子的本体论足以睥睨欧洲。儒者的求实精神,亦应有益于科学的建树。中国古时候不拥有发达的公理化系统。然而明朝已经引入欧几里德几何,亦未见科学之出现。大概总体语境不利于认识主体的成熟,似是一大问题。古汉语结构不需要系词,很难运用逻辑常词,也是大问题。除此之外缺少相对独立的常识一同体,与社会权力结构很难作出明智的抉择,也是问题。
到今天高唱不休的所谓天人合一,假如辨析不清,对国内的科学教育,弊病甚大。董仲舒的天人比附之说姑且不论,所谓天人合一,大概有天人一物和天人一理两派旧说。天人一物,似来自于庄子的所谓与万物为一体的神秘体验。程颢颇发挥之,如:“人与天地一物也。”“天人本无二,不必言合。”“只心便是天,尽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语录》十1、二上)陆王不必论矣。此种神秘体验,作为个人体验固无可非之,作为美学意境更是想法的一大源泉。然而如果是成为国民意识的一般语境,一直处于主客不分的囫囵状况,则不利于主体意识之成长,对于科学理性、契约精神、民权思想之培养,皆有妨碍。
所谓天人一理,则邵雍、张载、程伊、朱熹诸理学家皆发挥之,实为理学的一大理想。本义乃是指超越性的天理与人心的本性相通。如邵雍称:“能循天理动者,造化在我也。”(《皇极经世·观物外篇》)张载:“天大无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正蒙·大心》)此种理想,作为个人信仰亦佳。惟其中所已蕴涵的主客之分,与天人之分,总是让人忽视,而此种忽视在舆论中的弊害则甚大。中国文化中主客二分的思想,对于培养主体意识及科学理性十分有利,亦十分必要。天人一理的天,乃义理之天。既言天人,则天人已分。朱熹《仁说》:“泛言同体者,使人含糊昏缓,而无警切之功,其弊至于认物为己者有之。”又,《答江德功》:“知者吾心之知,理者事物之理。以此知彼,自有主宾之辨。”这主宾之分,十分要紧。将自然视为可以分解的物待之,才有科学。假如成日家泛言同体,惟有含糊昏缓而已,何时方能全方位揭示自然之奥秘?古人论主客二分的地方极多。譬如老子论为道,则主直觉,反用智,但论及察看万物,则明显主物我之分,与分门别类用心察看的科学精神。如:“万物并作,吾以观复。”“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哉?以此。”《墨经》论及主客及求知甚了解,如:“知,接也。”“智,智也者,以其知论物,而其知之也著,若明。”《荀子·解蔽》:“凡观物有疑,中心不定,则外物不清。吾虑不清,则未可定然否。”《天论》:“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故明于天人之分。”《韩非子·显学》:“无参验而必之者,愚也。”王冲《论衡·薄葬》:“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程颐:“致知在格物……须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积习既多,然后脱然自有贯通处。”(《语录》十八)王夫之《尚书引义》:“天与人异形离质,而所继者惟道也。”《读四书大全说·大学》:“大概格物之功,心官与耳目均用,学问为主,而思辩辅之,所思所辨者,皆其所学问之事。致知之功,则唯在心官思辩为主,而学问辅之,所学问者,乃以决其思辩之疑。”戴震《孟子字义疏证》:“事物之理,必就事物分析至微而后理得。”总之,以主体立场详细察看研究自然的精神,在中国文化中有着悠久传统,只不过没独立于人文学术而自成严密的逻辑体系而已。
自然与人的关系,既有对立紧张的一面,又有一体和谐的一面,需要全方位领悟,不能偏废。西方自中世纪将来,乃全倾向于对立与借助自然,于是视科学为对自然之权力。F.培根的名言最为代表:Ipsa scientia potestas est.(科学本身便是权力。) 中国传统则几乎顷全力于一体和谐之说,几只有老子指源于然的严厉:“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而古时候几乎只有荀子讲制天,亦即借助自然。事实上,人类的行为便蕴涵着天人二分与借助自然。人只须有消化管道,便不能不消耗自然资源。人只须有美化生活方法的需要,便不能不加剧消耗自然资源。因为西方的科学与价值脱节,对自然的片面领悟,与自我和消费主体的畸形膨胀,已经导致滥戕滥用自然,不考虑人类整体利益,毁坏人类存活环境的灾难性后果。
也恰恰在这里,有着中国文化理想的机会。国内文化传统有着恢弘深邃的内涵。文化的进步固然有着很多未知乃至非理性的原因,不可能简单地根据自觉意志的引导而进行。然而只须摆脱半殖民地文化自卑心理,不墨守冬烘式的国学陈规,而从人类历史趋向和当代人类需要的广阔视线去体认之,也就可能发现中国文化新生的机缘。科学,市场,法治,乃是现代人类社会具备普世性的体制,或许是人类历史不可抗拒的时尚。中国的文化理想,只须经过正确的诠解,可以提供现代人类需要的自然观、科学认识论和办法论原理。中国文化观念,既涵有主客二分、主体意识的思想,亦涵有天人和谐兼有人可制天的理念。中国人既把天视为可宰制可借助的对象,又视为自主的生命沃源。如《易·系辞》:“天地之大德曰生。”“生生之谓易。”《庄子·知北游》:“天不能不高,地不能不广, 日月不能不行,万物不能不昌。”董仲舒《春秋繁露·王道通》:“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不胜枚举。这便蕴涵着人与自然的主客互动的关系。同时,也觉得自然有着内在的理性性质,人可以认识而预期之。如荀子云:“天行有常。”“所志于天者,已其见象之可以期者矣。”“夫此有常以至其诚者也。”有常而诚,实即内在理性。《说文·言部》:“诚,信也。”而 《人部》:“信,诚也。”这里《说文》有循环概念的错误。《字汇·人部》:“信,不差爽也。”《广韵·震韵》:“信,验也。”不差爽而可验的常行,即秩序原则。实在之内的有常以至其诚,即世界内在理性也。对自然的认识,既要以经验的办法格一物复格一物地无穷反复进行,而最后理想又是类似统一场论式的全方位揭示:“惟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也。”真理的规范,便是人的理性原则与人所可能发现的自然秩序之间,无穷主客互动的对比。
结语
不同于技术,科学是精神创造活动。创造需要想法,而想法需要那生我养我的文化沃土为源泉。譬诸音乐,假如中国的作曲家恒常依据西洋的音乐动机去谱曲,能作出伟大音乐否?科学创造,其理一也。欧洲的人文理想曾孕育出一个年代的伟大科学。现在,那个年代的精神,也就是所谓现代性,已经显示出其局限性。而中国的文化精神却恰可补其不足,而取其所长。这里便涵有中国文化的机会。曾有人放言高论,称21世纪为中国的世纪。此语应作何解?“中国的”总不是possessive的意思吧。“中国的”似应指中国的贡献。贡献又在什么地方?仅仅亦步亦趋,可乎?仅仅“强大”,而无精神创造,可乎?没科学的伟大创造,可乎?于此可知中国的文化新生之重大意义矣。
中国的科学哲学家,不必斤斤于复述西方的理论,亦应以严格的形式化方法,创建新式的科学办法系统。中国的科学家,亦应汲取中国文化理念,创造新的科学理论。一二西方科学家已经在这样尝试。将人文理念,以自觉首要条件方法纳入科学理论的尝试尚属少见,然而更不是绝对没。如玻姆的量子力学理论便是。(见David Bohm, The Unpvided Universe: An ontological Interpretation of Quantum Theory, London,1993.)
这里便回到本文开头提到的人文与科学离别的问题。不论外部抑科学内部,对此种分裂现象,提供解决的渠道,皆不能离开教育的改进。中国的科学家,在其教育培养中,应同意中国文化的陶冶。其实,一般受教育的人,皆应同意此种陶冶,同时同意科学的洗礼。中学,至少高中,应设逻辑演算课程,与初步的科学思想概论。其语文课中的文言文比率可增至六七成,以思想为主,力避浮泛模糊之辞,以使少年早日窥见中国的宝贵思想,不致处处低伏于外来的无根思潮。大学低年级应设文理科共读的,与科学史相结合的科学办法论,与以中国为重点的世界思想简史。加之舆论的正确主张,或可培养出一代新人。21世纪中国怎么样之类的高论,或者稍有实践的基础。
科学与人文价值
点击数:978 | 发布时间:2025-03-06 | 来源:www.zvvzu.com
- THE END
声明:本站部分内容均来自互联网,如不慎侵害的您的权益,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
-
- 学习交流 -
-
欢迎加入中国人事人才网,与万千考友一起备考

- 成考路上不再孤单
专业院校
-
关注“考试直通车”
-
领取备考大礼包
-

点我咨询
返回顶部
Copyright©2018-2024 中国人事人才网(https://www.xftgo.com/)
All Rights Reserverd ICP备18037099号-1

-

中国人事人才网微博
-

中国人事人才网